
“我很小就开始画画,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个拉如。我天天地,月月地,年年地坐在画布前画佛像,为的是用自己的手艺帮别人积累功德……你要是真想学唐卡,那你就应该把笔记本放下。你就应该像我一样,坐在画布前面,三年、五年一直练下去谷锦网,直到你的手艺可以画出真正的佛像,让施主他们家(朝佛像)跪拜的时候能够真正地积德。”
人类学家薛茗自2009年起,便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展开自己关于热贡艺术的田野考察,在2024年出版的《77街的神龛》一书同名章节中她用文字讲述了相关的故事。在和唐卡画师们的接触中,她一度对画唐卡产生了兴趣,曾经好几次向一位唐卡画师提过出想要跟其学习这门手艺。起初,这位画师未曾给予回应,后来,薛茗再一次诚恳提出请求时,这位画师才严肃地对她说道,“你应该好好做你的研究,不要去画画!”之后他放下画笔,对薛茗讲出了开头的这段话。
在热贡,薛茗见到了许多唐卡画师,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在看似重复之中,也凝聚出了一种他者不易有的心力,从而让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交织出新的力量。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薛茗,一起从“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交织来理解生死。完整音频节目欢迎搜索“在川上”进行收听。
重复生活里的力量
小熊:在阅读《77街的神龛》这本书的时候,热贡这些唐卡画师画唐卡时的专注力很吸引我,在重复的过程里他们也获得了一种力量,这个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对生命和死生的理解,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主题。
薛茗:热贡艺术包括唐卡、堆绣、泥塑,2006年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成功申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也是这个时候踏入这片河谷的,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我接触到的这些画师们日复一日进行练习,在线稿本上打不同的线稿,每天练习度量,直到烂熟于心。与此同时,热贡艺术本身也发展出多元化的价值,一方面它是一个宗教艺术,另一方面它也要走入市场,这些画师也需要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他们在一个寻找和不太确定的状态下,和世界进行互动。他们在练习技艺的时候,是有一种确定性的,这也变成了他们信仰和生死观的一部分,但是进入到世俗市场里之后,又要面对不确定性。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处在有点迷茫、有点兴奋、有点害怕的状态里。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市场慢慢稳定下来,人们对唐卡追求的风潮也有点过去了,现在又趋于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当年我认识的很多年轻画师,现在已经自己带徒弟,有的人变成了大师,他们面临的又是新的挑战,要思考怎么把唐卡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来处理,如何让其艺术生命力延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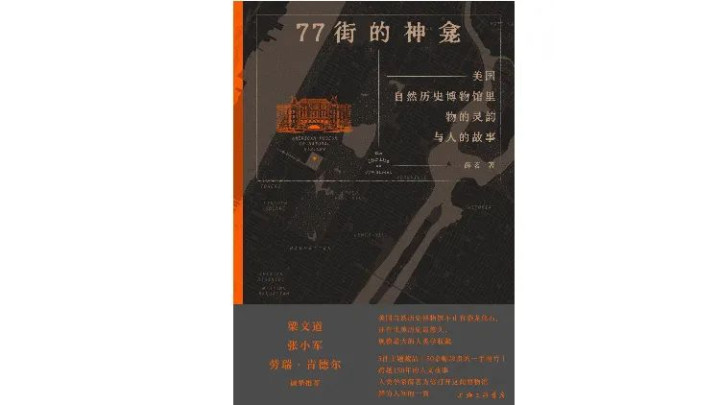
作者:薛茗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9月谷锦网
小熊:这样的描述,会让我想起中国上世纪90年代,而你第一次去到热贡是2009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时间差?
薛茗:是的,不管是从物质生活来说,还是文化氛围,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相对来说还是要发展得稍微慢一点。所以当时一下子激发了我的乡愁,我90年代在北京长大感受到的就是那种不确定性和激动的感觉,2009年来到热贡的村庄里面,我又重新感受到了人们的那种心境,是一种完全复刻的感觉。
人类学里没有绝对的客观
亚光:我很关心的是年轻的画师要怎么样在这样的时代更迭当中去定位自己,市场经济的潮流在冲击他们曾经的传统环境,而物质也是很现实的诉求甚至是诱惑。这让我想到去年很火的一部电影《破·地狱》,作为现代的殡葬行业从业者道生,在电影里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很难的。
薛茗:我现在正在北京798的空间站画廊做一个展览,叫做《灵性的指引》,可以契合上你说的这个话题。展览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出发,不是去讨论唐卡的审美价值或是艺术意义,是探究佛教造像艺术里面的这种生命力。这里面有大量画师的自我陈述,是他们自己对艺术、对作品、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展览会持续至8月10日。
话说回来,在布展的时候,会有一些展览需要的物品运过来,比如供水的碗,比如经书,还有一些小的唐卡。我就和大家说,这些东西不要放在地上,先放办公室的桌上。说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很多文化逻辑我已经内化了,不会简单把它们当成展览材料。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物,可是也有自身属性的力量在其中。

798空间站艺术中心展览《灵性的指引》,7月12日至8月10日展出进行中。图为薛茗正在讲解。
小熊:你作为人类学家,在做研究时是被要求不能做选择的;但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最后一定会有选择。
薛茗:我觉得对人类学家的这种要求其实也是挺虚伪的谷锦网,其实你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比如你拍一个纪录片,你的摄影机镜框就只有那么大,你就是要选择谁进入到镜头里面来,这已经是一种编辑了。所以我一直很反对说人类学里老是强调客观,我们最多只能做到方法论上的客观。
这是一个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可能把自己带有的所有的可能的偏见的原因展示出来,我从哪里来,我受过什么样的背景训练,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语境里长大的。所以我肯定带有我的偏见,那我跟你说清楚。同时我们也用更清醒、更平等的眼光和视角去和异己之人、异己之物相处。
亚光:博物馆的策展我觉得跟薛老师讲的人类学家做田野也是很类似的,如果说人类学家只能看到以他的视角呈现的那部分真实,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去呈现更多样的视角。博物馆也是如此,一个博物馆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穷尽所有的视角。

798空间站艺术中心展览《灵性的指引》,7月12日至8月10日展出进行中。
追寻物的生命史
薛茗:是的,我前阵子在上海图书馆做活动的时候,有个观众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现在短视频、多媒体这么广阔泛滥,对人类学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我给的回答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以前可能你只能靠马林诺夫斯基或者列维-斯特劳斯去给你阐释,现在当地人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可以直接和全世界的人去沟通,这对人类学家来说是一种监督,你不能自诩是所谓的专家就胡说八道,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重构了知识的生产过程。
小熊:但另一方面这可能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就是话语权的转变,我也在思考这种转变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大家会不会越来越趋向想成为kol,然后反向提供可能是受众想要听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要传递的东西。
亚光:是的,比如艺术家要追求独特性,但吊诡的是,现在往往是用从众的方式来实现的。
薛茗:这个现象人类学里很早就有,叫做自我东方主义。我是当地人,当外国人来了之后,我们为了显示民族文化里遥远的浪漫的形象,会穿上传统服饰,跳两段自己也不太会的舞蹈,尽管我们平时也是穿耐克球鞋。我的一位同事常年在韩国做萨满研究,她接触到大量的游客和艺术家,她就开玩笑说,这些艺术家有的比人类学博士生还勤勉,没事会去搜一搜论文,还会记下来专家对他们艺术的解释,下次有游客或是人类学家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下就变成权威了。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还会打开小本子拼命记。

2022年新翻修后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NH)北美西北海岸展厅。
亚光:薛老师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是怎么看待近年来的人类学热的?
薛茗:在我要出国留学的时代,哪怕当时在美国,人类学都是个很小众的领域。我当时在胡同里碰到一个老人,我说我要去读人类学博士,她说“人类学?是搞计划生育的吗?”包括去了美国,很多人也不了解,觉得学这个专业的人很学术很宅,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派对搭档。后来,人类学就变得特别流行,什么都可以加上人类学的标签。
说回人类学热,我很喜欢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里的一个比喻,他说人类学家做好了顶多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捣蛋鬼,你其实是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的,但你可以去刺激出很多问题,如果你有个疑惑去到博物馆,反而会有印象深刻的体验。
博物馆里的展品是有生命的,我们可以追问它从哪儿来,谁把它带来的,还可以去进一步探寻有没有和它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视角,去追寻物的生命史,而人的生命往往是由物的生命去定义的。所以像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无伤大雅的捣蛋鬼,顶多给大家提供多一种可能性,看到生命的另外一种角度。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心态就会更平和一些,更宽一些,因为我觉得不再是说我有一种执念,可能有些东西我会放下,但是有些东西我可能会觉得更珍惜。
小熊:不是说要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我们在探寻生命这段旅程中,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去寻找一个永远也找不到的答案。
亚光:人活着的很多意义,其实都是承载在物上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物的存在会比人类更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而物的背后一直也都有人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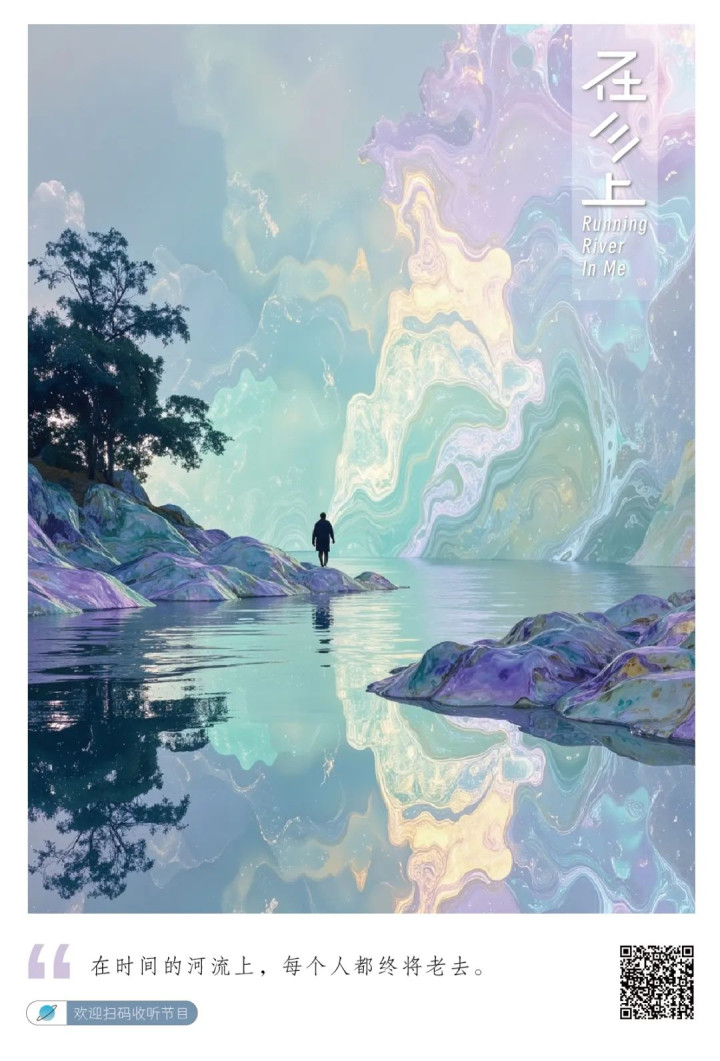
作者/小熊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谷锦网
通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